望潮
台州市委市政府唯一官方新闻客户端

“治世入仕,乱世归隐”,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选择。宋末元初,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,就有这样一位学者,隐居家乡,创立义塾,为远近的学子传道授业。他就是黄超然。
黄超然,字立道,号寿云,柔川(今黄岩区屿头乡)人。他一生未做官,只做个教书先生,以毕生精力教化乡邑子弟。他所创立的义塾,经其子黄中玉改建,成为了“柔川书院”,一时间,学生云集,弦歌不断。
元明以降,这所书院,一直是台州学子心目中的一片净土。

教书先生
黄超然生于南宋端平三年(1236),他的家族柔川黄氏,是黄岩的名门望族。
柔川黄氏的始祖黄懋,是北宋初年的大臣,官至工部尚书。他曾贬官至台州,游历柔川后,很喜欢当地的风景,就把家迁居到了这里。
黄超然是黄懋的十三世孙。他的父亲黄景龙在太学内舍任职,祖父黄应时是光山县(今属河南信阳)的县令。
黄超然自小好学,读书不舍昼夜,在同辈中属于佼佼者。他少年时,跟随蔡梦说、车瑾等学者习“濂洛之学”;青年时,又师从王柏,学“性理”,成为朱熹的再传弟子,学识也愈发深厚。
他两次由州县推荐,参加科举考试,均未中第。从此,他便不再向往官宦生活,以著书立言为己任。
黄超然读书涉猎甚广,既看老庄之书,也看孙吴兵法,对医学、卜算、农业等也有所涉及,间或衍生出新的看法。他治史严谨,往往对史料进行详实地考证,用事实来说话。
黄超然著作等身,著有《西清文集》十卷、《诗话》十卷、《笔谈》十卷、《地理撮要》十卷、《凝神会要历》十卷,以及《岁计录》中所记载的宾祭、工役、器用、施舍、周恤之宜二十条,每一条都可以应用。
著述,是留给后人的。黄超然曾说:“与其多述以诏后,曷若及吾身而面命乎?”意思是,与其多写书昭示后人,不如当下以身作则来影响学生。因此,他在乡里建起了义塾,自己当起了师范,只要有意愿读书的子弟,都可以来免费上学。

柔川书院在今黄岩屿头乡上凤村
诲人不倦
在学校,黄超然对学生管理严格,每天清早鸡鸣,就要起床洗漱,进入书斋读书,上午不得会见宾客及议论家事,必须到午后才可以。
黄超然诲人不倦,闲坐时庄重而静默。就连乡里的痞子,见到黄先生都有所收敛,甚至对他羡慕而崇拜。
元元贞二年(1296),黄超然过世,年六十岁。他的儿子黄中玉,继承了父亲的遗志,将义塾改建成了“柔川书院”。
书院中间设立祠堂,供奉程颢、程颐和朱熹,意味着将程朱理学奉为正宗。东西厢房作为师生的宿舍,后堂是讲课行礼的地方,厨房、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。后来,这座学院为州县里培养了不少人才。
元代台州的地方政府听说了黄超然办学的事迹,特地安排人到柔川书院考察,并为黄超然请谥“康敏”。“寿考且宁曰康,好古不怠曰敏”,长寿而好古的长者,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。为嘉奖他办学,为教育作出贡献,官方还将他的牌位入祀乡贤祠。
柔川也因为书院和黄氏家族的存在,而成为台州文人们的游历之地。据《柔川黄氏宗谱》记载,明代的状元秦鸣雷、刑部左侍郎王宗沐、南京吏部尚书何宽等,都在柔川留下足迹。
儒家理想
南宋末年,兵戈四起,黄超然却办起了书院,从表面上看,这似乎是迂阔之举。元代诗人、潞国公张翥却给了黄超然极高的评价。他认为,宋末盗贼的兴起,正是因为教化缺位,异端邪说因此乘虚而入,败坏了老百姓的道德之心。
黄超然身体力行推行教育,让人们知道有亲、有义、有别、有序,通过启迪心智,把人善良的一面激发出来。这对主政者而言也颇有启发,如果一个地方能注重基层教育,将会帮助人们去追寻更好的生活。
应该说,黄超然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,他用一生来践行心目中的儒家理想。
光阴易逝,柔川书院今何在?前段时间,在柔川黄氏后人黄福德的带领下,我们来到屿头乡上凤村,去寻找书院的踪迹,然而,早已无迹可寻。当地只留下一个“水院”的地名。据说,“水院”即“书院”,因为在黄岩的方言里,“水”与“书”同音。
黄超然墓,在屿头乡前礁村,距离南宋赵伯澐墓大约百米远。该墓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摧毁,其墓志铭今藏于黄岩区博物馆。

黄超然墓遗址
参考文献:《柔川书院记》/张翥
见微知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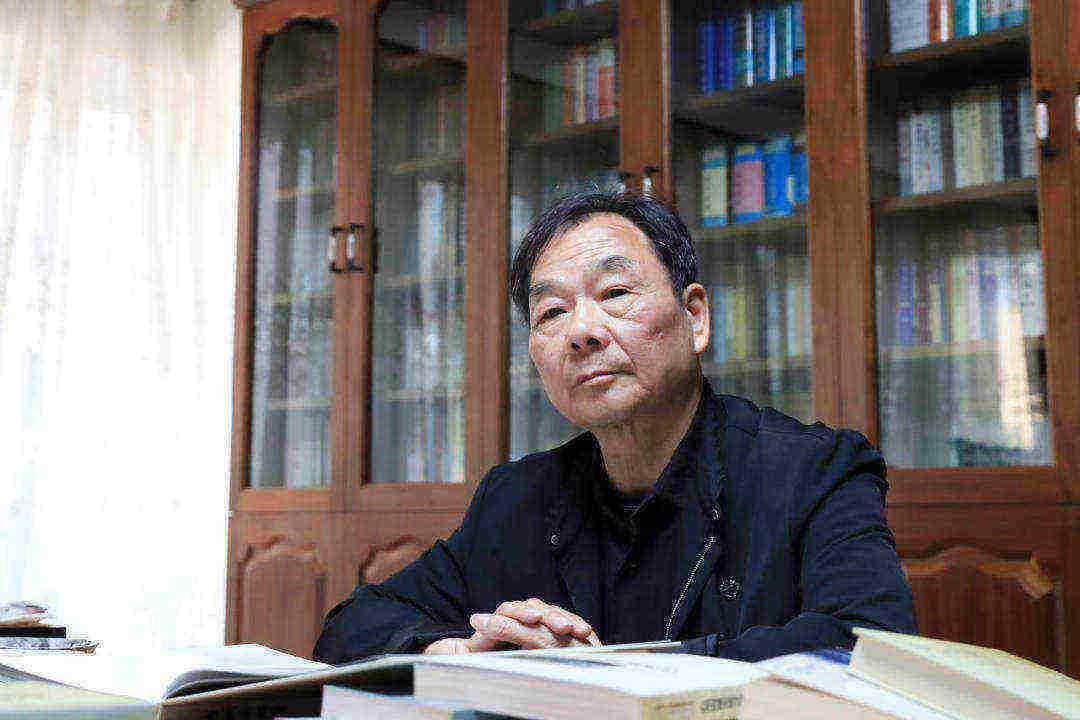
临海市博物馆原馆长、文史专家 徐三见
柔川书院是黄中玉于乃父黄超然所建私塾的基础上改建而成。中玉号初庵,他将私塾改建成书院,一是为了拓展乡里的教育,二是为了纪念与光耀其父的育人之功和学术建树。故而,中玉在营建书院时还专门于院中构建了祠堂,中间祀二程与朱子,傍则以乃父陪侍。
黄超然,字立道,号寿云,是上蔡书院王柏的重要弟子之一,学问深邃,著作等身:“文章华胄,诗礼名家,学贯六经,尤邃于《易》。安居恬静,不以贫窭动其心;性识高明,不以功名易其志。以博达之才,道德之化,渐于乡里也远;渊源之学,仁义之教,被于后人也深。故既殁而名益彰!”时人评价之高,于此可见一斑。显然,这样的评价绝非虚语。
即以他的居所为例,据寿云先生自言,“中年无所于巢,乃避于墙东之小屋”,这是居住之所。“小屋之西又有小屋,甚劣,如蜗牛之庐……松床竹几,萧然终日,抱一守中,以遗视听”,这是他的读书之所。如此陋屋,寿云先生还给它取了一个颇为动听的名字,榜曰“西清道院”。别人讥笑他说:“子屋甚陋,不得为道院,顾以道院名?院固无书,又自赞为读书之所,然则庄周、列御寇复生于今耶?”意思是这般自诩“如蜗牛之庐”为“道院”,岂不是像庄子、列子那样,说话不着边际了吗?死后当地行政长官疏请“赐谥康敏”,可谓名副其实。
往期链接
编辑:吴世渊
审核:诸葛晨晨
监制:于鹏
总监制:陈永渊